產品詳細介紹

帶上假發,披上長袍,一遍遍地練習著臺詞,爭取以后能在只能看到一次的觀眾面前,獻出完美的表演。可能是由他們扮演著的姐姐,一字一句飽含深情地傾訴著對妹妹和心上人的話語。可能是由他們,身披白色長袍作書生模樣,朝遠方踽踽獨行的老者跪下,目送敬重的先生離京。在這樣的劇本里,劇本殺復盤答案我們不僅感受著劇本里的故事,還有主持人、NPC們演繹出的視覺、聽覺沖擊。初看便是劇中人,再看已是看客心。他們讓我們更近一層地接觸劇本表達的意像,而脫離了這樣的環境,我們已無法再次體會和感受。哪怕回想偶有感慨,但要再回到當時激動的、強烈的情緒就有些難。或者是,一段由作者聽了無數遍的、契合劇本當時當刻的音樂。讓我們在劇本的文字外,得到聽覺的暗示,在不知不覺間被引領著進入作者創建的無形世界。音樂的力量是不容小覷的。而它帶我們進入的世界,在這場劇本游戲里,體會夠深刻。就好像,聽一首喜歡的電視劇插曲一般,往往在看電視時播起的這首曲子,比我們平時干聽,要來得感觸深刻。這是輕易的一次,能順著音樂走到它希望我們抵達的地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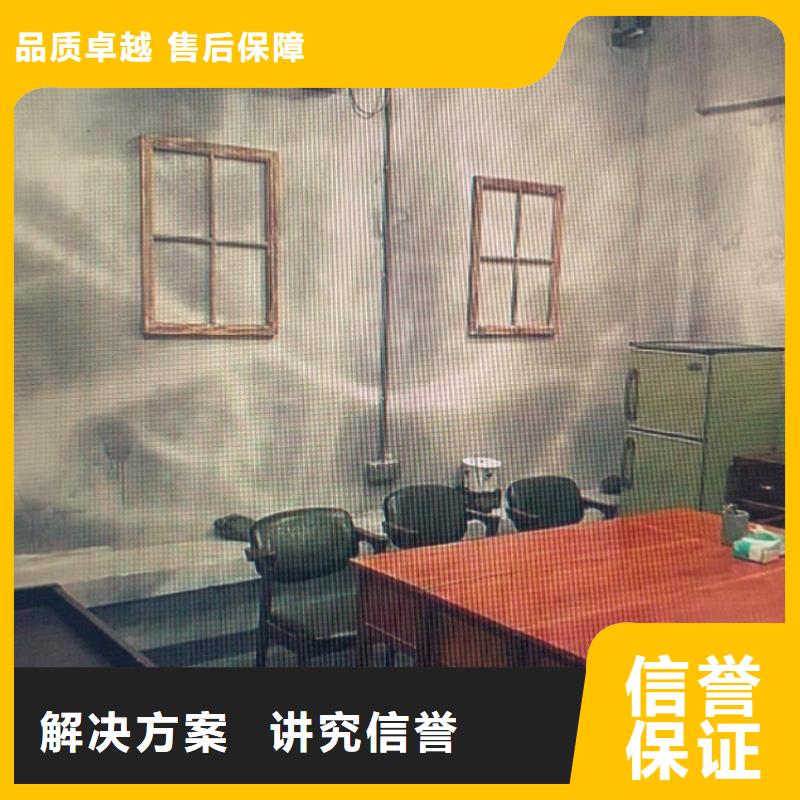
說完了概念、產業鏈,我們再回到那個關鍵問題,為什么那么多人喜歡玩劇本殺?首先,劇本殺本質上是情緒消費。玩家參與游戲過程中,大腦分泌多巴胺產生快樂情緒,玩家會為了這種愉悅感花錢體驗,這有點類似看話劇或玩狼人殺。但看話劇需要審美水平,狼人殺需要較強的邏輯和表達能力,相比之下,劇本殺只需要進入劇情,玩家即使“躺平”也能玩到。有參與感、有線下社交、低門檻,還能獲取快樂,這種形式確實會讓消費者喜歡。不過,情緒消費的另一面是,一旦情緒調動失敗,消費者會重新計算沉默成本,所以盡管當前劇本殺很火,劇本殺復盤解析但網絡上對劇本殺的評價褒貶不一,兩級分化。另外,劇本殺的代入感,可以滿足玩家逃離現實的需求,換句話說,劇本殺可以幫助玩家進行情感宣泄。一場沉浸式的游戲,從不同的人生經歷中獲得新的體驗和認知,而通過對角色的“移情”,玩家在現實生活中壓抑的情緒往往能夠在這種場景中得到很好的釋放。1942年,美國心理學家莫雷諾創立了心理劇治療。他相信人類是天生的演員,且具有自然的行動渴望,需要將內在的情感狀態表達出來,以親身的體驗來認識自我,認識世界。比如,年輕人初入職場,對職場、自己的認知不夠,于是工作中產生的很多情緒就被壓抑在心里。他認為自己能將這些情緒消化,但在一次“劇本殺”中,扮演的角色剛好是與他有類似經歷的年輕人。
“如今劇本殺已經成為風口,但不是風口上的所有人都能賺到錢。”一家知名劇本殺連鎖品牌負責人告訴《中國資訊周刊》,“目前國內的劇本殺行業還很年輕,行業門檻低,競爭很無序,盲目開店、三個月倒閉的案例比比皆是。在現階段,入行需慎重,‘躺賺’是不可能的。”劇本需求爆發感知到市場變化的是劇本殺的寫作者。從去年10月至今,群主王三三建立的一個劇本殺作者交流群從0迅速擴充至近500人,劇本殺復盤解析劇透測評真相答案兇手角色其中一半是90后,三分之一是00后。王三三告訴《中國資訊周刊》,這些劇本殺寫作者大多是寫網文小說、自媒體文案出身,也有兼職寫作的學生、上班族,一些早期作者或寫出了代表作品的作者已經拿到專職簽約,收入比普通作者高一大截。作者群體壯大的直接原因是劇本殺市場的需求爆發。由于劇本殺游戲的劇情特性,一個劇本玩家們通常只玩一次,即使是多支線、多結局的劇本,玩家二刷的概率也非常低。因此,隨著劇本殺行業的發展,市場對新劇本的需求日益旺盛,僅依靠從前那“一小撮”劇本殺作者的產量是遠遠不夠的。按照劇本殺的創作發行流程,通常是由作者原創一個劇本,交由編輯或監制評價修改,再由劇本殺店家組織測試,反饋意見后再修改,終定稿交由發行商印刷銷售。在收益結算上,作者可以拿到銷售額的20%~50%的分成,具體一個劇本的收益由劇本級別、作者名氣、銷售情況共同決定。據王三三介紹,目前市面上劇本銷售類型分為三種:本(一個城市僅有一家授權名額)、城市限定本(一個城市有三家授權名額)、盒裝本(不限量授權名額,只要想買都能買到)。三種劇本的質量要求不同,本高于城限本、高于盒裝本,相應的價格也不同,通常盒裝本定價在500元左右,城市限定本2000元左右,本則從5000元到20000元不等。
但在這兩點之外,是否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面對冰冷的機器和汪洋大海般的數字信息,人們似乎本能地對“身體不在場”感到焦慮。回顧傳播史,人與人的交流在突破身體的限制后,又不斷趨向“在場”,尋求聲音、圖像乃至VR、元宇宙。我們不難發現對一些重要的事,人們更傾向于“面談”,并不完全出于信息的考慮,而是因為“身體在場”對人類交流的特殊意義。劇本殺復盤解析劇透測評真相答案兇手角色這早或可追溯到《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對文字的不信任,后來德里達將其展開,“事實上,修辭術專家早已成為‘詭辯者’:一個不在場的人,一個不真實的人”。在場和真實被聯系起來。而電子媒介相對文字更易刪改,也就更讓人懷疑它的真實性,這種懷疑也從媒介本身曼延至其背后的主體。傳播學者約翰·彼得斯認為,到了電子媒介時代,交流從克服身體觸摸靈魂,“變成了跨越中介性的靈魂去觸摸另一個人的身體”(虛擬的劇本角色或可視作一種靈魂中介)。以上說法,似乎都表明“身體在場”暗含著某種“情感紐帶”,或是“真實”的保證。玩家們約定并讓渡一段時間是劇本殺開始的前提,相較“無情”的數字信號,具身交流更加連貫,也更加“親密”,共度的時間不可復制粘貼,人也不能同時“在場”兩個地方,由此“身體在場”被賦予信息之外的“不可替代的儀式意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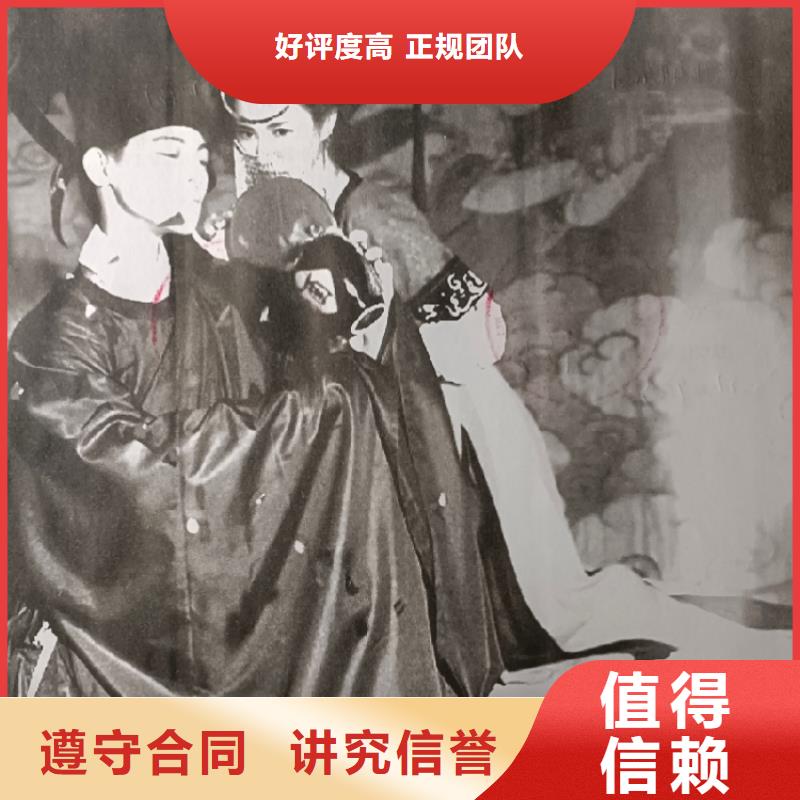
 17za.com
17z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