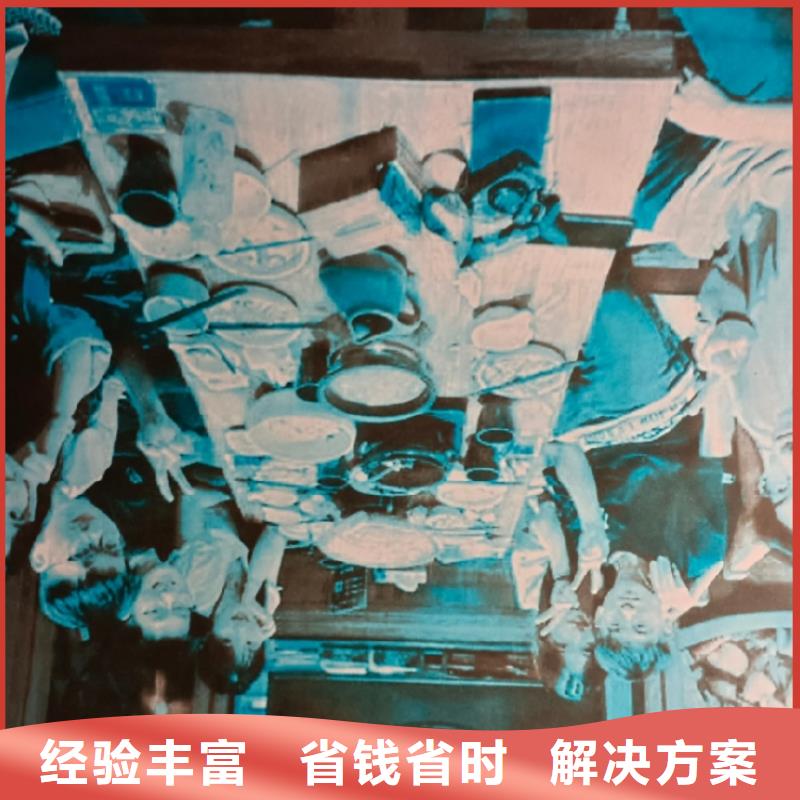2021年的夏天,既是劇本殺行業的火熱之夏,亦是大浪淘沙,洗牌迭代之夏。當下劇本殺行業內的產業鏈條已然分明清晰,作者-發行-展會-店家,這四個產業鏈條上的環節,正各自面對著當下行業內部趨勢變化帶來的影響。劇本殺的編劇有點不一樣對于內容創作者而言,劇本殺是一條更加自由精彩的創作之路。不像傳統的小說和網文寫作那樣,動輒耗時一年半載;也不需要像創作影視劇本需要平衡各方意見且上線周期漫長。靠一個的劇本殺作品獲利數百萬,早已是行業內部認可的神話,而超級口碑作品如《年輪》的后續影視版權收入更是令作者和發行振奮。在行業飛速發展的當下,一個尚處于草稿階段的劇本殺,只要在某一方面有亮點,就足以令許多發行趨之若鶩。盡管如此,就像每個行業都有其獨特的行業壁壘,劇本殺創作對于編劇也有獨到的要求。劇本殺復盤解析劇透測評真相答案兇手角色首先,與傳統的影視甚至文學作品不同,傳統創作者所擅長的將沖突集中于C位角色身上的技巧,恰恰是劇本殺創作者需要反其道而行之的——作者必須兼顧游戲中每一位玩家的感受,力求使每個人在事件中的戲份相對均等,或通過不同的視角立場看待事件,或通過不同的選擇分支改變事件。如果劇本中出現過多的邊緣角色,則一定會遭到玩家的詬病。
柳瑩對此表示并不擔心。“目前,高級玩家大都不帶新人。倘若劇本殺從業者也不肯投入、投身其中培養新人的話,新舊玩家將會產生斷層,這不利于行業的發展。搞到,誰都得不到好處。”柳瑩表示,盡管不能要求“高玩”對“小白”更加包容,但劇本殺館的經營者可以從自身做起“孵化”新手玩家,只有用戶規模繼續快速增長,才能保證整個行業的蓬勃發展。“所以,我會經常分享這種理念,希望經營者們都行動起來!劇本殺復盤解析劇透測評真相答案兇手角色”【結束語】可以說,劇本殺行業除了DM創作者需要培養,新人玩家同樣也需要 “孵化”。受限于劇本殺的游戲特性,圈子潛在的“鄙視鏈”短時間內難以。因此“孵化”新人玩家的任務,便落在劇本殺館經營者身上。換句話說,劇本殺館“孵化”新手“小白”可能會給別人做了嫁衣,但越來越多的經營者參與進來,培養的就是全行業未來的忠實用戶群體。
如果從兒童劇本殺本身來看,“游戲+學科+價值觀引導”的新形式,確實給傳統教培行業轉型設計了一條新路徑。
專做兒童沉浸式戲劇的瞇呱教育創始人吳雨橋表示,孩子需要學習,但對孩子來說,游戲是輕松的,學習是沉悶的,這使得學習和孩子天然對立,成了不少教培機構和家長面臨的困境之一。而在劇本推理的過程中,孩子通過游戲學古詩、做算術,這或許是解決上述困境的新思路。
王城對此表達了相同觀點。兒童劇本殺,本質也是一種課堂輔助手段。王城稱,頭部教培機構都會在課程中引入積分兌換、游戲升級獎章等趣味性的內容,其目的就是讓學生愿意進入課堂。“讓學生主動進入課堂是關鍵的一步,學生愿意學,即使沒有名師上課,學習效果也會較為顯著。”
沉浸式兒童劇本殺平臺萌探劇游亦表示,不少教培機構找他們定制適宜6-12歲兒童的系列劇本,引入價值觀塑造和職業選擇的新內容。
“兒童劇本殺這種教育屬性在下沉市場表現得更加明顯。”吳雨橋介紹道,據其了解到的情況,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僅在山西省陽泉縣,一家教培機構一個月內就開了20場劇本殺活動。在更為下沉的福建省福州市某“十八線”的小縣城,一個月8場活動,同樣場場爆滿。
吳雨橋表示,兒童劇本殺在下沉城市更為走紅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其新穎的形式對家長的吸引力較大。另一方面,在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下沉市場,兒童劇本能夠在短短2個小時內,串聯重要的知識點和學科考點,教學效果極容易形成“一傳十,十傳百”的口碑外化。
不過,盡管劇本殺本身去教室化、能夠與戶外營地、舞臺藝術等場景相結合的特性,確實讓兒童劇本殺的新故事越來越多。但如果現在就斷定,兒童劇本殺是教培機構轉型的新出路,目前來看,還為時尚早。
不過,安媽也表示,盡管已經有部分教培機構原意嘗試開展兒童劇本殺活動,但更多的教培機構仍處于觀望的狀態中。劇本殺復盤答案
教培機構的觀望,背后其實是本經濟賬。徘徊在是否轉型中的王城表示,如果將兒童劇本殺作為一項增值服務,單日活動過萬的營收確實吸引力很大。“可一旦轉型成專門的劇本體驗館,卻要面臨裝修、人員等巨額成本的支出,算算這本經濟賬,不少教培機構的負責人,很難下定決心徹底轉型。”
另外,現階段教培機構傾向于把兒童劇本殺作為一種銷課手段。如半日營一次銷課2-3節,一日營一次銷課6-7節,同時單個學生還能額外營收至少200元。吳雨橋則直言,“不僅不用專門裝修,還可以利用現有的場地、生源和員工,為校區迅速產生資金流。”
但與此同時,對于一些教培機構利用兒童劇本殺迅速回流資金的方式,吳雨橋坦言,目前兒童劇本殺面臨的問題,就是創作劇本和推動活動的教培機構多數是投機者。
“急功近利的心理,導致部分教培機構只求快圖新,但不注重效果外化,周一買本,當周就計劃開本。”安媽同樣表示,不少教培機構只關注某個機構通過一個現象級劇本實現高盈利的個例,寄希望于購買單個劇本,或者試圖通過打造單個劇本實現轉型。但結果往往是,劇本買回去只做了兩場活動,就難以為繼。
海德格爾曾寫到,“打字機是一片沒有標記的云彩”,“使人手喪失了本質地位,而人類卻沒有完全體會到這種剝離”。隨著媒介的泛濫,我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這種“剝離”,感受到線下課堂與線上教學,現場演唱會與直播演唱會之間的差異。智能手機的普及更讓虛擬世界的通道變得“信手拈來”,數字的幽靈無時不在,這不僅使我們能“脫離”身體傳遞信息,并形成了一種主動或被動的“依賴”。我們被“不真實”的文字、影像所淹沒,身體仿佛成為一個不知如何安置的“多余物”,與之相應的是,人被“簡化”成信息。劇本殺復盤解析劇透測評真相答案兇手角色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當下的很多年輕人而言,劇本殺可能是他們說話多的時候,也可能是他們遠離手機久的時候。從中我們不難看到年輕人對具身交流的渴望,渴望暫時“擺脫”作為傳播中介的機器,而不愿一直做賽博空間的“幽靈”。在凱瑟琳·海勒看來,“身體還是幽靈”的選擇背后是信息與物質性的關系變化。電子媒介不斷突破物質載體的限制,延續數千年的“形態”被迅速取代,人們對物質世界的存續感到“擔憂”。起初的焦慮來自打字機對手的剝離,但海德格爾也解釋打字機并不是真正的機器,而是一個“過渡性”產品。更大的焦慮來自計算機對“在場”的剝離——人是否能被首先理解為“一套信息程序”?在此背景下,曾經人們試圖“克服”的身體,似乎成為一個重要且不容退讓的“界線”,作為某種“生命”的確證。回到劇本殺,“在場”對交流的意義已無需多言。值得追問的是,就像打字機是工具與機器之間的過渡產品,劇本殺是否也可能是一種“中間態”?如果元宇宙在技術上更加成熟,能夠“虛擬”身體,讓人真正地“忘我”,或者人與機器充分結合,成為“賽博格”,那么“身體在場”對我們又意味著什么?這些相關的問題,值得研究者繼續追問和探究。